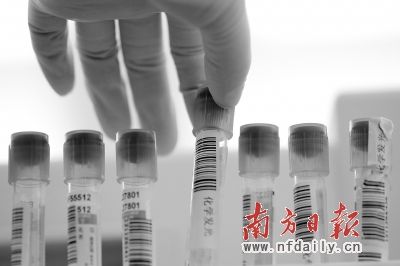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防艾现状»
抗艾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已开始。这场斗争此消彼长,至今未分高下。 在此过程中,1981年12月1日在美国加州确认的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挫败感,它就是艾滋病(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会攻陷人类免疫系统,并发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及肿瘤,严重者可致死亡综合征。 刚刚过去的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的最新数据,去年,全球仍有3400万艾滋病病毒(简称HIV)感染者,其中新增感染者250万,17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在广东,截至今年10月,全省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病人37723例,其中病人12605例、死亡8957例。 30年来,伴随着人们“恐艾”情绪不断增长的是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尽管成功的艾滋病疫苗迟迟未能面世,但是,如鸡尾酒疗法、基因疗法等手段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为艾滋病的治疗投递缕缕曙光。 在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艾滋病防治24年的陈小平看来,艾滋病防治30年的征途正如人类的太空探索计划: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不断碰壁,也不断前行。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通讯员 朱丹萍 策划统筹:赵威 徐林 在黑暗中守望 这是灾难片的经典桥段:一种死亡率极高的未知病毒突然爆发,大批感染者迅速死亡,世界陷入恐慌。在全人类危在旦夕时,一种疫苗终于被成功研制出来,人类最终得救! 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上,疫苗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881年5月5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用实验成功证明疫苗是如此有效以来,人类已经成功研发出上百种疫苗,有效地控制了多种传染病。 因此,人类对艾滋病疫苗研究期望甚高。然而,30年过去了,艾滋病疫苗每到呼之欲出时,却又最终让人希望落空。科学家们提出了种种方案,经过临床试验,又不得不无奈地宣布: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 按传统的疫苗制备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HIV疫苗。因为如果对HIV病毒进行灭活,便会失去免疫原性。如果仅仅进行减毒操作,那么HIV疫苗随时可能复活,增加接种者感染风险。 如果疫苗是一种武器,那么在保护人类健康的斗争中,它带来了辉煌的战绩:借助疫苗,人类消灭了肆虐数千年、造成数亿人死亡的天花,这是人类消灭的第一种传染病。麻疹、风疹、腮腺炎、白喉、破伤风、黄热病、流感、乙肝等疾病也因疫苗而臣服人类。 然而说起疫苗的工作机制,您可能会大吃一惊:它不仅不能直接保护我们,反倒可能会攻击我们。疫苗接种其实就是主动用病原体感染人体的过程。“将经过人工减毒或灭活的病原微生物注入人体,通过适应性免疫,产生对这些病原体特异的免疫反应。”陈小平将此比喻为人体进行的一次次防病演习,“通过演习学到了生存技能,当真正的病毒前来侵犯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主动将其拒之门外,防止感染。” 自1881年5月5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用实验成功证明疫苗是如此有效并可自主研究以来,人类已经成功研发上百种疫苗,有效地控制了多种传染病。 正因如此,人类信心满满。上世纪80年代初,在首次分离出HIV病毒后,时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Margaret Heckler公开表态,将在2年内研制出艾滋病疫苗。 没想到卡壳了! 疫苗的制备有几种传统思路。一方面,可以利用减毒的活病原体,黄热病、麻疹、风疹疫苗等属于此类疫苗;也可以由灭活的病原体制备,例如流感、霍乱、甲肝疫苗等。此外,破伤风和白喉疫苗是利用病原体灭活的类毒素制备的,而乙肝疫苗则是利用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蛋白制备而成。 但按传统的疫苗制备方法根本不能获得有效的HIV疫苗。因为如果对HIV病毒进行灭活,便会失去免疫原性。如果仅仅进行减毒操作,那么HIV疫苗随时可能复活,大大增加了接种者感染风险。 随着生物医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出现,如今人们对疫苗的作用原理有了远超前人的洞见。 科学家们意识到,疫苗必须有免疫原性,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时获得针对特定细菌或病毒的体液免疫(诱导抗体)和细胞免疫(激活免疫细胞)。前者是通过造出抗体蛋白,在血液中认出特殊的病原体,如HIV,并抢先在它感染人体细胞前抑制它的活性;后者是在病原体感染了细胞之后产生的免疫反应,目的在于认出并销毁已被感染的自体细胞,这样病毒就失去了存活条件,也不能复制增殖进而感染其他健康细胞。 “此前研究是比较割裂的,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对HIV疫苗来说,两种免疫反应都很重要,因此,如今的研究正逐渐打破之前各自为政的状态,试图将诱导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结合起来,寻找艾滋病疫苗的新道路。”陈小平说。 但至今,科学家还没有任何办法在非实验室条件下引起抗体反应即体液免疫,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这难如登天。 屡战屡败,是否此路不通? 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免疫学教授帕特里斯·德布雷对此有个较为“乐观”的说法:艾滋病是一个时间和努力问题;或许应造就一位新学者,他将以自己的研究促成巴斯德革命和遗传学革命的综合。如果我们其他医生在拖延时间,那不是因为我们受困于过时的概念,而是我们缺少巴斯德! 病毒狡猾 HIV病毒具有极强的变异性,陈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研发出候选疫苗,病毒变异后,免疫反应也已经认不出最新的病毒,。 30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念,但最终能够突出重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仅有3类:衣壳蛋白重组蛋白疫苗(AIDSVAX);利用减毒后的活腺病毒为运输工具,能表达三种HIV基因的疫苗(V520);利用金丝雀痘病毒,表达HIV基因片段的疫苗(RV144)。 “三种疫苗中最被寄予厚望的是RV144,它一度被视为人类战胜艾滋病的救星。”在泰国进行的大规模人群实验发现,这一疫苗能够减少26%的HIV感染。一时间,“艾滋病终结时代来临”等标题登上报纸头条。 但这一结论很快遭到质疑,RV144的有效性被视为“统计学的诡计”,即统计结论高于实际表现。最终,这个耗费了美国一家公司近十亿美元的疫苗黯然退场。 既然疫苗曾经战无不胜,为何唯独艾滋病疫苗始终难产? “首先,HIV病毒具有极强的变异性,像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陈小平表示,人类每年都要研发新型的流感疫苗,就是因为流感病毒变异性很强,而HIV病毒的变异速度比流感病毒还要快100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研发出候选疫苗,病毒变异后,免疫反应也已经认不出最新的病毒了。” HIV病毒的狡猾之处还在于,它的攻击目标直击人体免疫系统的要害CD4 T细胞。这是人类免疫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细胞,被HIV病毒入侵后,时间长了,免疫系统将被摧毁。 这也是为何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例感染艾滋病而自愈的病人。此前,即便是凶残如天花的传染病,也总有几例幸存者,为天花疫苗的研究提供了样本。 无人幸存的事实让科学家们不禁怀疑:是否人体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完全抵抗HIV感染?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即便疫苗具有免疫原性,能够调动人体的体液和细胞免疫,但肯定无法产生足够的保护作用。 长期、持续的病原体暴露也让疫苗的作用大打折扣。很多人小学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学校突然有很多人得腮腺炎,大家被紧急接种疫苗,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因为对病毒的接触是短期的,所以控制相对容易。但对于潜在的HIV病毒感染者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每天都接触到病毒,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研发出疫苗,其保护作用也让人堪忧。 在光明中前行 一边是作为重要预防手段的疫苗研究屡屡碰壁;另一边,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的数字,2011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3400万人。人类似乎正面临着被艾滋病前后夹击的窘境。 在摄影师Kristen Ashburn的镜头下,津巴布韦的艾滋病孤儿骨瘦如柴,被皮肤紧紧包裹的条条肋骨清晰可见,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同样的命运。而津巴布韦并非孤例。 幸运的是,相较于疫苗研究,艾滋病的治疗手段正不断更新,捷报频传。尤其是华裔科学家 此外,基因疗法也日渐为全球科学家所重视。陈小平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进行基因治疗研究,期待着能为饱受煎熬的艾滋病患者带来福音。 服“鸡尾酒” 只用一种药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变化就可以存活,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那就试试联合用药。因为类似于鸡尾酒的调制方法,才有了这样带有浪漫色彩的名称。 美国篮球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因其一手绝妙的传球功夫有着“魔术师”之称。然而,在1991年的一场记者会上,他无奈地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消息公开后,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约翰逊篮球生涯的终结,更是提前宣布了他的“死刑”。 然而,21年之后,53岁的约翰逊仍旧顽强地活着,并且担任了体育评论员、商人、艾滋病活动家等一系列职务。篮球世界的“魔术师”,在对抗艾滋病病毒时,表现得也像魔术师一样不可思议。 约翰逊神奇背后的秘密,正是何大一和他的鸡尾酒疗法,即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何大一如此陈述鸡尾酒疗法的基本原理:如果只用一种药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变化就可以存活,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为何不试试联合用药? “简单来说,每个单药都对艾滋病病毒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但由于艾滋病病毒变异能力极强,较容易产生对某个药物的耐药性,采取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方法,能显著降低病毒耐药发生率。”陈小平解释。 鸡尾酒疗法将两大类已有的抗艾滋病药物(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中的2—4种组合在一起使用,这种联合用药的方法类似鸡尾酒的调制,因此有了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名称。 鸡尾酒疗法证明了“治疗就是预防”的理念,因为能够消灭人体内的大量艾滋病病毒,这一疗法可将异性间艾滋病传染几率降低96%。据陈小平介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如能按照此种疗法坚持服药,能基本实现艾滋病人的零死亡。 然而,较昂贵的费用让发展中国家的不少患者难以坚持下去。“毕竟,这就好比得了糖尿病,需要终身治疗,但是费用更加昂贵,肯定有患者吃不消。”陈小平坦言,鸡尾酒疗法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这一疗法并不能完全清除体内的病毒;其次,长期服药容易带来恶心、贫血、肾结石等副作用。” 基因“敲除” 今后有可能将艾滋病患者的头发或皮肤细胞诱导成iPS细胞,再敲除其CCR5基因,并进一步将其诱导成造血干细胞,回输给同一个病人,用于治疗或治愈艾滋病。 科学家们在艾滋病防治的征途上苦苦探索30年,却从未出现一例痊愈的个案。就在全人类的“恐艾”情绪不断蔓延的时候,首个艾滋病痊愈病例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现。 这名“幸运儿”是一位生活在德国的美国人,名叫蒂莫西·布朗,既是一名白血病人,也是患病十余年的艾滋病人。2007年,为了治疗白血病,布朗在德国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没想到,术后他的新骨髓产生了对HIV病毒具有免疫能力的新细胞。经过20个月的观察,主治医生格罗·许特曼宣布患者再没有显现任何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迹象。 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功给医学界带来极大鼓舞,基因疗法研究的重要地位日渐凸显。 “基因疗法可溯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注意到,非洲的一些性工作者长期跟HIV携带者发生性关系,却始终不被感染。”陈小平介绍,随后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的免疫细胞内缺乏CCR5受体,而这一受体正是HIV病毒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辅助受体。 陈小平领导的研究循此思路展开。今年2月,该小组在《人类基因疗法》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用锌指核酸酶技术敲除来自病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是通过基因转染技术将某些转录因子导入动物或人的体细胞,使体细胞直接重构成为胚胎干细胞的多潜能细胞)的CCR5基因,并将这种缺失CCR5基因的iPS细胞成功地诱导成造血干细胞。 陈小平透露,后续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中。现在,研究小组计划直接从感染艾滋病的猴子身上提取造血干细胞,进行CCR5基因的敲除操作后,再回输给同一个猴子,以检验实验效果。 展望这项研究的潜在应用前景,陈小平说,如果获得突破,今后有可能将艾滋病患者的头发或皮肤细胞诱导成iPS细胞,再敲除其CCR5基因,并进一步将其诱导成造血干细胞,回输给同一个病人,用于治疗或治愈艾滋病。 小知识 那些年,我们研究过的抗艾疫苗 DNA疫苗 这种疫苗包含了部分HIV基因和一些无害细菌的DNA。当它在1989年首次问世时,研究者相信它能够带来一场疫苗革命。因为这种疫苗不仅在老鼠身上引起了免疫反应,而且生产起来既简单又便宜。遗憾的是,其人体试验最终宣告失败,因为它几乎没有一点实质效果。 活载体疫苗 它使用一种无害病毒作为载体将HIV病毒的一部分基因载入。按照载体的不同,这类疫苗的研究衍生众多分支,其中,一种使用减毒后的腺病毒(常见的感冒病毒)的疫苗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活载体疫苗,然而它也在2007年9月被确认无效。 肽疫苗或脂肽疫苗 这种疫苗包括了HIV病毒的一些片段,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免疫反应。近期,法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制出了和脂肪分子相连的肽链,有助于增强疫苗的致免疫力,目前正处于实验阶段。 治疗性疫苗 |